《王的盛宴》首次媒体专访,陆川面对七大质疑(《电影》杂志2012年3月刊封面人物,采访:杨天东)
- 体育资讯
- 2024-12-28 00:03:28
- 7
采访/杨天东
采访手记
好莱坞的剧作教科书一再告诉我们:故事不是讲述困境,而是于困境之中人物的选择。在《南京南京》上映的那些天,陆川几乎成了舆论风暴的中心。然而两年之后,陆川不惧争议,再度出发,触碰人尽皆知的历史题材楚汉争霸。直觉告诉我,陆川,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
挖掘漩涡中的灵魂是艺术作品的力量所在,也是媒体人的良知所向。于是,在众多的选题计划中,我向主编申请了这个专访,并得到她极大的支持。
探寻陆川,有很多词可以描述,但唯一不能回避的是“质疑”。这个刚过完41岁生日的年轻人,从第一部电影《寻枪》开始,便将“质疑”的精神浇筑在他的电影创作中,到了《南京南京》,这种质疑上升到对“历史真相”的探究。在电影中,他质疑人生,质疑历史。同时,他的作品精神人格也被质疑着。但正如他所说的,质疑本身就是一个进步。
采访陆川,不仅需要体力,更是个脑力活儿。因为你知道,喜欢“质疑”的导演一定会给采访者增加心理压力,这也是为什么电影记者不敢轻易触碰姜文的原因。为了做足功课,我几乎把所有关于陆川的采访资料翻个底朝天。看着陆川回答的每一句话,我都会在心里猜想,面对各种质疑,他的内心经历怎样的一种起伏。
有了这些准备之后,当天的采访气氛异常的好。他告诉我,这是为《王的盛宴》做的首次正式专访。
通常情况下,记者最惧怕两类被采访对象:一种是夸夸其谈型,这样的人虽然不至于让你冷场尴尬,但他说的每句话都是隔靴搔痒,永远只能触及事实层面,绝没有任何真知灼见,这种稿子编起来神经松弛、味同嚼蜡;还有一种是惜字如金型,他的回答比你的问话更简练,他把你当成了假想敌,这样的采访如同作战,往往是两败俱伤。对于第一种人,我通常不会打断他,而第二种人,我会选择跟他一同沉默,事后用些许文字去填补那些“留白”。
陆川当然不归属于这两类。在近四个小时的对谈中,面对“质疑”二字,陆川冷静地梳理着自己的行走轨迹,动情地披露了他的心路历程。谈艺术创作,他像个训练有素的演讲者,逻辑清晰,有理有据,回到最有争议的质疑话题时,他又变得小心翼翼,从内心生发出一种感动或是激愤。他不伪装强大,亦不放低姿态,却像一个朋友,跟你讲述这些年的遭遇与心迹。
在采访过程中,随着他的讲述,我似乎与他一同卷入那些争议和质疑中。待我从他的讲述中走出来,一时有些许恍惚。我一再想,是媒体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了陆川?还是陆川的个人行为影响了媒体的选择?这些我都无从判断,就如同陆川本人所言,这个时代已经开始从一个盲从的时代进入一个质疑的时代。如果说我能为这些质疑做点什么的话,但愿这篇采访能为公众还原一个相对真实的陆川!
质疑一:陆川又拍了一部《鸿门宴》?
回应:“这次是我为这部电影接受的第一次正式的采访,属于我们电影即将启幕特别重要的一个采访,所以特别想通过你们杂志向所有观众和读者说一句话,《王的盛宴》不是鸿门宴,他是讲一个时代的命运,讲一批人的命运,它完全不是一顿饭……”
MOVIE:听说你最近一直在做《王的盛宴》的剪辑,现在剪到什么地步了?
陆川:已经精剪了五遍了,还在剪。这次剪辑给我带来的体验不太一样,我觉得我现在刚刚摸到电影的一个基本的边界。现在刚刚开始心里有一些底,知道该怎么去做这个电影。
MOVIE:这个“底”是指什么?
陆川:以前我剪片的方式就是关起门来剪,《寻枪》一直剪到自己认为非常好的时候,再给资方看,那个时候资方也提不出什么意见了,也就定剪了。这一次做电影的方式也改变了,编剪从初稿开始就有资方的介入,包括国外发行方也过来看片。所以编剪听到大量的意见,有中肯的,也有批评的,我突然发现这种争论对我帮助很大。因为在这个阶段,你已经听到最难听的和最肉麻的话,自己也知道该怎么去做这个东西。不像以前,在《南京南京》、《可可西里》上映前,心理都是完全茫然的。
MOVIE:它会是一个多少分钟的片子?
陆川:片长还在逐渐缩短,从当初的两个半小时到现在的两小时十分钟,我觉得最后可能会在两小时左右,不会太长。
MOVIE:你说自己为这个片子做了很多功课,展示了这两年考古过程当中的新发现,跟以前的主流想法不太一样,能不能说一件不一样的事情?
陆川:我不太想谈具体的考古上的新发现,其实每一个发现都包含着巨大的争论。但我觉得这个时代特别好,它已经开始从一个盲从的时代进入一个质疑的时代,我们开始质疑以往的知识、以往的真理。有这种质疑说明这个社会开始进步了。单说考古学这一项学科,从来没有像今天被这么多人知道。以前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发掘了一个墓,大家都鼓掌,但现在发掘一个墓,就会出现一个声音——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比如说曹操墓。这是为什么我不需要去说很多具体的例子的原因,现在的每一个事实,它要成为真理进入教科书的话,都要经受一个质疑的过程。以往一些成功的经验也在被质疑,比如说秦始皇兵马俑是否是秦始皇的,从秦始皇兵马俑被公布开始就有像陈景元这样的学者一直在质疑,他的声音也被压抑了几十年,现在他已经开始在国内出书了,开始详细讲解他的160多条质疑。
MOVIE:回到电影本身,你所说的这种新发现,在电影怎么体现的?
陆川:我们绝大部分的历史片,百分之七八十、百分之八九十都属于武侠片,绝大多数是跟历史没有关系的科幻电影,飞来飞去,里边的历史观,我觉得基本上是跟历史没有太大关系的,只不过是套一层戏服而已,而且还不是古人。我觉得历史中实际上隐藏着很多秘密,对于秘密的揭示还不够。还有一些历史片拍得非常好,但他趋同于一种主流的观念,他们没有拿出一种新的观点。这些都让我觉得,关于历史的电影实际上还有可以做的空间,其实我们到了一个必须重新认知我们自身历史的一个阶段。中国的历史是这样的,每朝每代都会去改写历史,所以很多真相就在改写或者说拆建中被淹没了,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去梳理历史真相,重新梳理中国人的历史观,所以我对这个挺有好奇心的。
MOVIE:能不能说一两个细节方面的东西?
陆川:关于历史的电影还是要跟历史有相关的,至少我的信念是要重建一部分历史,要重建一部分当时的人文历史的景观。比如说在我的戏里边,吃饭是不用筷子,而是用手抓,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筷子很长,是用来捞大的罐里边的肉,把它夹起来,但真正吃饭是手,往嘴里塞一把饭,然后用手指头蘸酱,抹在嘴里——类似情况,我们都有复原。还有鸿门宴上的仪程,可能对于别的电影来说不重要,但对我们还是比较重要,还有一些细节如鸿门宴是在账篷里吃还是在宫殿里吃,上的什么菜品。这部戏其实不是大制作,所以有一些东西能做到、有一些东西不能做到。我们只能在细节上下功夫,比如鱼的尺寸,那个鱼可能会比较大,那时候你看汉代的画像砖上,鱼和人体的比例,除了艺术夸张之外,鱼和人的比例基本上是一比一。你想一下就知道,那个时候水里有一条跟人一样大的鱼很正常,所以我们端上的鱼也很大。类似点点滴滴,电影里出现的所有器物都是出土文物的复制品,复制了大量的道具。
MOVIE:这是历史文化与景观这一块儿,在影片的戏剧性上,怎么体现出来?
陆川:在戏剧性这块儿,我也觉得确实很累,这段历史实际上是耳熟能详的故事。那耳熟能详的东西为什么要再去拍一遍,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就没有去讲,我不关注那些东西,我比较关注在官方历史记载字缝里隐藏的东西;这个电影出来之后,估计会有一点儿像《南京南京》,会引起争议。
MOVIE:据说,吕后会作为剧中重要的角色贯穿故事的始末,而这个吕后的扮演者恰恰是秦岚。鸿门宴的故事基本上是一场男人之间的争斗吧。你有没有想过,观众可能会跳出电影之外去想这个电影。
陆川:首先我们这个电影它不是“鸿门宴”,这也是为什么它没叫《鸿门宴》的原因,我们叫《王的盛宴》。这次是我为这部电影接受的第一次正式的采访,属于我们电影即将启幕特别重要的一个采访,所以特别想通过你们杂志向所有观众和读者说一句话,《王的盛宴》不是鸿门宴,他是讲一个时代的命运,讲一批人的命运,他完全不是一顿饭,但这顿饭我拍了,完全按照《史记》里边的记载,但同时又是在《史记》的字缝里边找到了鸿门宴的秘密去重拍了这场戏,你会看到跟《史记》描述非常逼近的鸿门宴,又是在《史记》的字缝里边找到那个时候隐秘的、司马迁不能去写的东西。但是对于电影来说,这绝对不是讲鸿门宴这一顿饭的。所以吕后作为这段历史贯穿始终的人物,她显然很重要。在历史上,吕后从刘邦起义时就变卖家产帮着刘邦,到最后杀韩信等一系列的事情都是吕后主持的,所以她是在刘邦身边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伙伴,这是历史,历史就是这样的。
MOVIE:这会是一部女性电影吗?
陆川:不是,他是一部男性电影,主要是刘邦、项羽、韩信、箫何、张良等人的故事。因为刘邦是一条线,所以吕后自然而然戏份要比其他的女性重一些。
MOVIE:《王的盛宴》要表达什么?
陆川:现在还不能说,这得看。
MOVIE:你慢工出细活在业内是出名的,所以大家叫你“陆漫漫”,《王的盛宴》从去年的三月份一直拍到十一月份。八个月时间无论是对投资方还是演员的档期这块儿来说,都是压力,有没有想过凑合着拍完算了?
陆川:我们选的拍摄地象山去年一直在下暴雨,各种雨各种台风。我是不愿意凑合,比如说一场戏应该是阴天的气氛,如果是晴天,可能我会选择等。这在以前拍电影是很正常的,在电影厂时代,为了天气去等很正常,现在几乎不等,有什么是什么,赶工期省钱。我只觉得,现在我还等得起,我还能扛,有一天我等不起的时候我就不等了。在我有能力去支撑的时候,我还是希望把电影拍好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得对得起观众,观众就是一次性消费买票看一个东西,为他们做多好都值得。慢工细作其实对谁都没有什么好处,尤其是对我,唯独对观众好。我愿意接受所有的批评。其实我可以拍得很快,《寻枪》33天就拍完了,拍得快很容易,就像我写《黑洞》的时候,一天一集。其实我现场手脚很利落,不是那种犹犹豫豫,但如果有一些东西达不到我的要求,我会要求返工。
MOVIE:有人说,片子曾经停工过,这消息准确吗?
陆川:其实说实话,从开机到结束,因为资金断裂停工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因为去等天气,比如说明天下通告单拍阴天戏,突然到了现场是晴天,像这样的等是有,但从来没有说停工。这个行业就是这么一个行业,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但我觉得像《梅兰芳》也拍八个月,很多戏都拍得长,可能作为年轻导演你需要面对这些质疑,我觉得也很正常。
质疑二:陆川的话有煽动性
回应:“这个话痨的习惯其实是在军校养成的。原来我在高中的时候说话就脸红”。
MOVIE:据说你是看了张艺谋的《红高粱》之后才决定拍电影的?
陆川:基本上可以这么说。
MOVIE:你还记得当时看这部电影的情景么?
陆川:我在劲松,就是《红高粱》上映那一年,当时我很小,我记得票价两毛钱,应该是中午或是下午,好像是星期天,看完后就崩溃了。因为我在中学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文学家,写小说。看了之后突然觉得电影比文学更有力量,电影的表达是语言、声音、画面、音乐综合在一起的,像洪水猛兽一样,无法抵挡。其实《红高粱》我只看过一遍,到现在为止差不多已经有快三十年了,里边的很多场面还历历在目,还能完全背出来,包括台词和结尾,因为到结尾的时候,你会觉得坐到椅子上站不起来,银幕里有一个巨大的手把你按在座位上。所以,《红高粱》的观感影响了我做电影,我永远都希望我的电影结尾能够让观众站不起来,这种力量一定要有,或者走出影院的时候能带着一部完美电影的感受离开影院,这特别重要。否则你跟观众的这一次恋爱就失败了。
MOVIE:为什么只有《红高粱》给你传递这种感觉?
陆川:以前的中国片也看了特别多,也有喜欢的,像《小兵张嘎》、《冰山上来客》各种黑白电影,但都是挠你,我觉得《红高粱》从他的颠轿开始,到高粱地姜文和巩俐的野合,再到酿酒,让我第一次看到电影是讲什么的,电影是在讲生命力,不是玩规则。我觉得以前电影都是四平八稳,给你讲一个东西,有很强烈的主观意识。《红高粱》你不能去形容它,它是一个野兽,其实在我看来,它讲抗日也是一张皮而已,它为了在中国当时的体制下能够去讲这个,它想讲的其实是欲望,讲的是生命力的绽放、喷发,你不能去描绘,但能感受。当然现在的电影多了,现在是一个欲望可以泛滥的时代,在八几年清教徒的那么一个时代,安安静静的一个时代,突然看到这么一个东西,我是当场崩溃了,被吞噬了,我觉得那是我想去做的东西,而且他很浩大,又不小资,我自己非常喜欢,虽然很多人在批评,但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MOVIE:据说,大学的时候你就想考电影学院,但是你爸让你选择读军校?
陆川:对。因为那年正好是89年,他可能觉得在军校比较安全,不会到处乱跑。
MOVIE:这对你后来从事电影有什么影响?
陆川:我们军校其实是学国际关系的,学英语,我真的是觉得,那对我的生命来说是一个惊喜,我们那些老师都特别喜欢电影,上精读泛读课的时候,老拿各种英语的名片给我们放。其实上那个学校看了很多电影,我印象最深的是《飞跃疯人院》,还有《毕业生》。那四年,在精神上是自由的,但是在纪律管理上都是纯军事化的。其实是很拧巴的四年,但我觉得受益匪浅。今天我看了一下你们的采访提纲,其中有一条是我为什么特别能说,这个话痨的习惯其实是在军校养成的。原来我在高中的时候说话就脸红,进了军校,可能是因为自己画画还行,变成军人委员会宣传部部长,让我去干各种活,我就开始从出板报到办报纸到排节目当编导,都是一肩挑,就得说很多话,这语言能力肯定是那一会儿练出来的。
MOVIE:在大学的四年当中,电影的梦还一直在做着么?
陆川:电影滋养没有断,但是电影梦断了,因为将来我们从事的工作太跟电影没关系了。我大学毕业后直接分到军队,后来才偷偷地去考电影学院的研究生。因为想最后试一下,因为那个时候感觉船离岸越来越远了,想最后跳一下能不能跳到岸上去,要不然这辈子肯定是军人,走不了,因为我们单位也特殊,要工作下去就要保密。
质疑三:《寻枪》应该是姜文的作品
回应:“在《寻枪》中,所有我想表达的东西我都表达了。里边既有姜文老师他习惯的一种东西,但也会有非常年轻的东西出来,这就是两个创作者都把自己的东西撂进去了,不是谁把谁彻底地给淹没了或者阉了”。
MOVIE:你研究生毕业之后去了北影厂是吗?
陆川:电影学院毕业就分到北影厂。
MOVIE:你说三年没有导过一部作品,当时你在做什么?
陆川:做梦吧。一直想导电影,一直在写剧本投稿。
MOVIE:怎么等到第一部电影的机会?
陆川:其实那一段时间写了很多剧本,前后都写了很多剧本,就投稿。像《寻枪》这个本子直接就可以卖给很多导演,但当时还是想留着自己拍。我觉得用“等”这个词好像是主动的,其实是被动的。你投稿到一个指定公司,然后几个礼拜没有消息,再投下一个公司,又几个礼拜,其实一年有几个礼拜,很快就过去了。在这中间,我写了《黑洞》以及另外一个电视剧,为了赚钱付房租。其实也挺羡慕同学的,当时在租的房子里,经常听到同学去中央六套拍了什么电视电影,还有拍电视剧的,其实那会儿能拍东西就很幸福了。
MOVIE:是不是听到身边的人都混得有声有色,自己内心会很焦虑?
陆川:羡慕嫉妒吧,恨没有。因为你会恐慌,你怕被这个社会忘了。当时我在一个筒子楼里边租了一个特别小的房子,就在月季园,北太平庄那一块儿。每天到报亭开始卖晚报的时候就出去转几圈,然后整天在屋里待着,宅着,也没有人找你,电话从来不响,电话响一下,找你聊聊事,就特激动。基本上手机一个月不响一次,没人理你,那种日子太可怕了,但现在特盼望那种日子,整天待着,没人理你。现在想象那个时候要是能再准备更多的东西,写更多的东西,看更多的书,其实现在爆发得会更好,可能在创作中间会更好,其实现在恰恰缺的就是重新充电的时间,重新看书、看片子的时间。
MOVIE:是不是得知有人给你投资拍《寻枪》的时候感觉终于见到太阳了?
陆川:那个过程太漫长了,回答你的问题我就说一个事,开机那天是在贵阳青岩镇上,他们在庙里放鞭炮。当时姜文、我、制片主任等所有人都在院里放鞭炮,开机了,然后我觉得特别茫然,啊,当导演了。等了三年突然就开始拍片子了,你会觉得特茫然,特别不可信这个事,就很激动。因为姜老师拍了很多片子,但他在现场也是很会张罗的那种人,我印象很深,他在那儿张罗大家拍照、点鞭炮,所有人都很欢乐唱歌的时候我就从那儿出来了,找了一个角落淡定了一会儿,我感觉像做梦一样,突然是导演了,之前你做编剧,但在这一天以后,你就是一个电影导演了,觉得特不真实。
MOVIE:之前不是有过广告现场拍摄的经验么?
陆川:那个有,但那个完全不值得提,没有电影的那种神圣感。我为什么拍电影特别较真,因为对我来说太难了,我拍第一部戏的时候已经30岁了,你会觉得这会是像一个宗教一样,你信任他十几年,终于成为一个教徒,逐渐地开始操控这个事的时候,真的要对得起这个事,所以就挺较真的,是那种感觉。
MOVIE:据说你写剧本的方法比较特别,比如,之前在做《寻枪》的时候,找了一些网络影评人一起来讨论剧本。
陆川:因为那个时候在家待着没事干,我就是网络影评人之一,那个时候我们有一帮人都在新浪影行天下,每天在那儿聊,都是网友,大家都特热爱电影。后来我做第一部戏的时候,我肯定要跟他们在一起聊,不是把他们当作网络影评人,那个时候,哪有这个概念,就是贴吧的网友,大家一块儿出出主意,结交了一批好朋友。他们中间很多人现在都已经成为了电影的从业人员。
MOVIE:现在的工作方式发生改变了吗?
陆川:现在还是会给各种人看剧本,因为现在不再玩贴吧了,给网友看的这个事儿没有了,还是会给不同的朋友看,但我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真的很怀念,那个时候挺棒的。
MOVIE:你是个怀旧的人。
陆川:应该说非常是。
MOVIE:一般情况下,你的创作是先有故事还是先有一个人物,或者像香港导演们有一个细节就开始编了?
陆川:这几个剧本创作的起点都不一样,因为《寻枪》是改编人家的小说,肯定是先有故事。《可可西里》是先有了这么一个概念,有一帮人在那儿艰苦执着地保护藏羚羊但是没有人管,就这样一个概念,想去挖掘一下。到了《南京南京》实际上也是一个概念,想了解一个被死亡包围的城市。我的电影可能更多的是从概念入手吧。
MOVIE:在中国这一拨导演中,不论是对电影的这种狂热感,还是影片的去叙事性,我觉得你跟姜文有些像的地方。尤其是你的第一部片子,姜文在其中扮演了个重要的角色。
陆川:姜文是我一个特别好的启蒙老师,也是我在道路上一个很重要的帮助者。他在我最想要拍电影的时候,给了我一臂之力,让我跨进了大门。而且我在跟他合作过程中,实际上跟他学了很多东西,我们俩的电影观不太一样,非常不一样,电影的叙事技巧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我从他身上学到了两个东西特别重要:一个是创作者对电影的执着,第二就是对细节的追求。其实我以前是比较马大哈的人,但是他在拍电影前,对细节的追求让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想做有品质电影的导演必须要去做的事情。其实要从他身上学的东西特别多,包括表演,对演员的控制,很多东西我都会自己去思考,但是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两个。
MOVIE:有人说,你在拍《寻枪》的时候,姜文的干涉过多,让你感到很沮丧?
陆川:跟姜文合作,如果不觉得压抑,你就不是一个有追求的导演。因为姜老师,他是那种疯狂的创作者,他想进入所有细节的创作,不管他干什么,做演员时又想干导演的事,当导演时又想干演员的事,他想进入电影方方面面的创作,不管他自己的电影还是别人的电影,他跟每一个导演合作都会有类似情况出现。我在当时感觉确实有一点儿不习惯,这是肯定的,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很压抑。但因为我在军校待过,这就是军校给我的东西,军校也很压抑,但军队还是锻炼了我的毅力。我在跟姜文老师合作过程中,我觉得有一点对得起自己对电影的信念,就是在《寻枪》中所有我想表达的东西我都表达了。里边既有姜文老师他习惯的一种东西,但也会有非常年轻的东西出来,这就是两个创作者都把自己的东西撂进去了,不是谁把谁彻底地给淹没了,给阉割了。我做到了自己的表达,也非常坚强地存在了《寻枪》里边。这个经历对我后来做《可可西里》、《南京南京》帮助挺大。当有人跟你说不同意见的时候,实际上是帮助你电影做得更对,因为一个人的意见容易跑偏,几种意见的合力平衡下来的一种方向,一种正确的、更厚实的方向。尤其是后来拍《可可西里》的时候,因为刚结束《寻枪》的拍摄,那个反差太大了,在《可可西里》的剧组,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不会受到任何干扰。但那个时候我恰恰很想念姜文,我就希望有这么一个人每天跟你吵,每天跟你拍桌子,现在你的对手就是自己,其他人基本上不跟你对话。到了《南京南京》就稍微适应了这种状态。
MOVIE:电影圈中,除了姜文之外,还有哪些人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陆川:田壮壮导演,黄建新导演,当然还有韩爷,韩三平,这几个对我影响特别大。精神上的导师,我觉得应该是像田导和黄导,特别是田导。因为我是个特别冲动的人,一冲动就惹事,但是田导身上那种恬然淡定的东西,每次都让我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所以我特别愿意跟他聊天。我本身是个很懒的人,不爱走动,但是田壮壮导演是我特别愿意走到他身边去坐一会儿的那种人,什么都不聊,感受一下就行了。记得小时候气功盛行的时候,北京很多人围着树采气,你在田壮壮身边会被他的气场所感染,我身边像这样的朋友田导是一个。
质疑四:陆川喜欢哗众取宠的题材
回应:“我还是想把自己最真切的看法表露出来”。
MOVIE:你的每一部电影都因敏感题材而有可能面临政策审查的难题,比如说《寻枪》中警察丢枪,《可可西里》涉及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现状,《南京南京》又要面临棘手的外交问题。你曾经说过一句话——当你真诚地与这个体制对话的时候,相信一切都不会是壁垒。
陆川:我的一般做法是先拍,然后再想审查的事。因为我觉得很多电影提前想审查的事,就别拍了,中国的审查不是写在桌面上的条文,这个事是你很难预估的东西,政策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我不会去把审查当作我创作中的一个障碍,因为这样的话你拍不了戏了。我不会委屈自己去删节或者说去自我审查,我不会自我阉割。每个人的说法或者说每个人的态度都是根据自己的生命经验来的,从《寻枪》到《可可西里》到《南京南京》,我是尊重体制的,我按照所有报批流程走,我也不会因为他们一时不通过,就拿出去放,我会一直跟他们交流,一直跟他们沟通,然后我们一直去协商哪些东西可以最大限度保留下来,最终电影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出来,这是我的一个工作态度,这也是我在军校学到的,你要去交流,这是你在中国做事必须有的一个态度。
MOVIE:《寻枪》前后改了九稿,《南京南京》改了十四稿,包括《可可西里》将近改了一半,后来,投资方之一的哥伦比亚公司先后六次要求你修改结尾。到了拍摄现场还要大规模改剧本,通常来说不是一个职业导演做的事情,尤其你在《可可西里》还是第二部作品的时候就敢这样做。你的胆量来自什么地方?
陆川:这个剧本是我自己写的,我自己很清楚,剧本到那个结尾的时候,就是在假high,我写了一个好人抓到坏人的故事,然后所有人都开始高兴,但是那个故事放到可可西里,就像一个照妖镜一样,它告诉你这个电影就是一个谎言,你是实在没有办法坚持下去拍这个东西。另外我在电影学院研究电影史,中国现在有几百部电影,好莱坞也是很多,每年全球几千部电影,90%以上都是职业导演拍的,可是这些片子,很多没有跟观众见面的机会,也没有被人拿出来继续讨论的机会。当时我拍《可可西里》的时候也很纠结,我拍出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来,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谎言,这对我来说接受不了。所以开始拍了没多久,我就知道这个剧本一定要改。
MOVIE:有没有想着要拍出两个结尾出来?
陆川:没有,我从来不给自己这种机会。我觉得最好的结局就是队长死。因为到了那儿,你想当英雄,你想当代表,活下来的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在那么一个绝境当中你想坚持一个理想,当一个理想主义者没有希望。
MOVIE:当时做了这样的修改时,现场制片没有意见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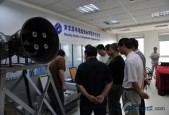







有话要说...